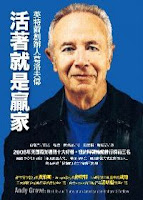
「去研究調查,自己做結論,不要把任何一項建議當做絕對的真理」--葛洛夫(Andy Groff).p.265.活著就是贏家第十七章
這本由葛洛夫(Andy Groff)口述的傳記,當中的第十七章描寫了葛洛夫如何對抗攝護腺癌的過程,使我印象十分深刻。不只是展現了「資訊不對稱」是如何影響醫療關係以及病人面對疾病的態度。而那種一生不停地面對現實、著眼於解決問題、實事求是追求真相、並勇於逆向操作的創業家精神,更是令我十分感動。
葛洛夫近六十歲左右,1995年,首度確定罹患攝護腺癌。一開始,他只是想自己多了解一下這個疾病,因此應用了在六0年代做矽研究的精神,,直接尋找第一手的原始研究論文,從零學起。當他發現當時,不同科別醫師之間對攝護腺的治療方式,卻是沒有共識,而病人術後的生活品質和後遺症的評估,也是醫師與病人的反應兩極,便決定自己動手研究。
醫學研究一方面基於倫理原則,不可能做真正亂數地決定病人治療方式,一方面,醫師的經驗與偏好也會影響結果,例如:醫師有可能會選擇病人身體情況能負荷開刀,或是疾病本身較有可能經由開刀治癒的病人進行開刀。如此自然造成,使用另一種療法的病人都是結果比較差的。
因此葛洛夫為了克服這種選樣偏差,收集足夠的人數以達到統計上的意義。又因為醫學人員不太會將自己的研究結果與其它人的結果比較,而這在半導體研究是標準實務,所以他不斷地將這些收集到的研究結果做交叉比對。在一連串的自我研究之後,他自己做了一張「資產負債表」來評估所有治療方式的優缺點,不管當時的黃金標準療法是什麼(Golden Standard),從中選擇符合自己需求的治療方式。他對結果十分滿意。(註:自1972年英國學者Cochrane提出實證醫學的概念,千禧年以來醫學研究也逐漸重視嚴謹客觀的樣本選取與交叉比對。)
就醫過程中,眾醫師從未遇過這種挑戰醫病權力地位的癌症病人,但也因他收集許多第一手資料並自行製作圖表,他也才能與醫師平等地交換意見。甚至在接受放療過程中,他還問技術人員進行放療的電腦CPU是那一種的。得到的回答是二八六,但那時Intel的奔騰(Pentium)早已上市兩年了。
在公開抗癌過程之後,葛洛夫成了自學抗癌成功的專家。他的例子也使我不禁在想,如果醫師本身不相信病人能理性地做決定,而病人本身也放棄面對現實與選擇的權利或是無法取得足夠資訊,那醫病關係必然是無法跳出父權關係。
全站熱搜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